作者:鲫鱼豆腐汤
2025/09/03发表于:sis001
字数:7,283 字
第十一章:夜泊鬼舫
苏夜白自从得了墨娘为伴,画技与心境皆日渐精进。
只是墨娘终究是魂体,长久地寄身于画卷之内,仍然需要「人气」的滋养。
为此,苏夜白便时常将那幅《素衣吟月图》卷起,于夜间带在身边,一同游
览霖安城的城郭。
这一晚,他们二人来到了绕城而过的「夜泊河」畔。
这条河白日里是千帆竞渡、货运繁忙的交通要道;而一入夜,便摇身变成了
这富庶之地的销金之窟。
甫一靠近南岸码头,那喧嚣的人声与奢华的灯火便如同热浪扑面而来。
只见河面之上,有数十艘雕梁画栋的豪华画舫往来穿梭,明角灯将整片水域
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,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丝竹管弦之悠扬、行酒猜令之豪放、莺歌燕语之娇俏,种种声浪交织盘旋不绝于耳,竟然将夏夜的虫鸣与风声都给彻底地压了下去。
画中的墨娘沉默了半晌,河面上过于炽烈的光晕似乎让她有些不适。
过了很久,方才用带着几分疏离的声调轻声说道:「在百年之前,此地的水
汽是清冽的,澄净的江面如同白练。
夜间唯有渔火二三,与天上疏星相互映照,方有能照见「月照孤舟」的冷寂
之趣。」
她接着的话锋微微一转,语气中染上难以察觉的惋惜:「而今这般,竟是将
天地间的清辉与幽寂都驱赶殆尽了。
这般汲汲营营的声势,美则美矣,只是却失了真意,落了下乘。」
「当真是,换了人间。」
她慨叹的余音还未散去,便被岸边码头上一阵更鼎沸的声浪所淹没了。
只见那码头上人头攒动,全都是是些衣着华贵的富商巨贾、佩刀挂剑的江湖
豪客,他们正争先恐后地等候着登船。
人群中不时传来几句高谈阔论,声音一个比一个响亮,仿佛要将那画舫上的
丝竹声都给压下去:「王员外出手阔绰!我听闻方才在「锦绣舫」,那柄前朝的
玉如意竟被他以三百两拍了去!」
「那又算得了什么?李公子今夜与人在「天香舫」上对赌,一注便下了一百
两黄金!」
苏夜白听着这些动辄千金的豪赌,再摸了摸自己袖中那几两用来买茶点的碎
银,两相对比之下,不免哑然失笑。
画中的墨娘似被他的笑意感染,那清冷的声线里也透出一份人间烟火气的莞
尔:「如此繁华,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句旧诗,『瑶台璎琳,皆有其价;仙宫咫尺,
凡人无路』。公子,看来你我今夜便只能充当那隔岸观火之人了。」
苏夜白正想要回应,忽然看见一艘最为瑰丽的画舫,劈开倒映着灯火的金色
水波,如一座浮华不夜的水上仙阙般缓缓驶近。
船上觥筹交错,影摇歌扇,宾客尽欢,一切看起来,都完美地诠释了何为
「人间乐土」。
然而,就在那画舫离得足够近,近到能数清歌女云鬓上的珠钗步摇的时候,
苏夜白脸上闲适笑意却倏然冷却。
在他的眼中,那船竟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。
那悦耳的丝竹之声,变得如同鬼魅的呢喃,空洞而诡异;满船的珍馐佳酿,
竟嗅不出半分香气。
再看那些船夫歌女,方才还笑容可掬,此刻细看,却是个个面色青白。
他们脚步虚浮,周身缠绕着一股驱不散的湿冷阴气。
这种情绪上的骤然变化也清晰地透过画卷,传递给了其中的墨娘。
「公子?这船有什么不妥之处吗?」
苏夜白目光一凛,他一字一句地轻声说道:「船是好船,景也是好景……」
「只是这船上,有鬼。」
二人正交谈间,异变陡生!
河中央最大的一艘画舫,其上灯火在此刻骤然尽数熄灭!船身猛地一滞,如
同被无形巨手死死攥住,戛然钉死在原地!
这毫无征兆的剧烈顿挫,瞬间撕裂了所有虚妄的欢宴。
船楼内玉碎瓷迸,哗啦作响,酒浆果馔泼洒一地;方才的管弦之声被一片惊
声尖叫与惊怒交加的厉声呵问彻底取代。
「怎么回事!」
「稳住!船夫都死到哪里去了?!」
「哎呦!我的袍子!」
河水剧烈翻腾,推搡着失控的画舫使其左倾右斜,更引得船上哭爹喊娘,乱
作一团。
就在这片凡俗混乱的正中央。
一位身披苔衣、须发皆为水草的老河神从浊水中缓缓升腾而起。
那些惊慌失措的宾客对此毫无察觉,依旧对着空气与流水叫骂不休。
他无视了船上凡人的骚动,那宛若实质的目光死死盯住船头那掌舵的青面船
夫。
其声如闷雷炸响:「大胆孽障!你们竟敢驱使这种污秽的鬼力,来玷污我的
清流!」
那青面船夫的魂体被这蕴含神威的怒喝震得几欲溃散,扑倒在地,叩首不止:
「河神老爷息怒!非是小鬼自作主张,实在是……实在是身不由己啊!」
「还敢狡辩!」
河神怒喝打断,「往日里,你们虽然使用鬼力,却还知道收敛,不过就是让
船快一些、静一些!我念在你们也是可怜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也罢了!」
他巨大的手掌猛地指向那艘画舫,指尖水汽凝聚:「可今日你们竟敢在
此处布下邪阵来窃夺整条水脉的灵气,以此供养那迷惑人心神的邪法,好让凡人嬉戏!」
苏夜白闻言凝神望去,果然看见画舫吃水线之下,似乎有数道幽暗的符文随
着水波若隐若现。
「水脉枯竭一寸,我的身体便会损伤一分!」
河神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金石崩裂般的怒意与痛楚:「你们真当我是泥塑
的木偶,毫无知觉吗?!」
「河神老爷明鉴!我等皆是沉溺此河的孤魂野鬼,受那百年冰水蚀骨之刑乃
是天定的命数!可恨那『金道人』,他先是用重入轮回的虚假言语来诓骗我们,
引诱我等签下那逃不脱的卖身契;再施行那邪法将我等的残魂与这船炼在了一处,
永世不得超生!」
「他逼我等日夜驱动这『汲灵水阵』,偷来的灵气都输送到舫心那盏琉璃灯
里,去维持什么『幻梦术』,让那些客人醉生梦死,才好赚上他们的金银啊!」
「说起来真是可笑可悲。生前为人奔波劳碌,卖命换那几两糊口的银钱;死
后成了鬼,竟还是换了个地方当牛做马!永无出头之日!求河神老爷……垂怜啊!」
老河神听完这番血泪控诉,那由水流构成的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。
他环顾着这片被「买卖」二字熏得油腻污浊的水域,目光最终落回那些瑟瑟
发抖的可怜虫身上。
他周身水汽如沸,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。
然而那澎湃的力量却在触及某种无形界限的瞬间,硬生生倒卷回流,未能向
画舫倾泻分毫。
他滔天的怒火,在一声几乎要将整条河都压得下沉的漫长叹息中,被强行摁
熄。
「此间的孽债,根须已扎上岸,缠入了霖安城的滚滚红尘。」
老河神的声音低沉下去,「我只能管辖这水里的事情。至于水上的船,船上
的人,以及人所订立的契约,都并非是我所能够触及的。」
「你们……自求多福吧……」言罢,神躯便欲化水散去。
就在那神影即将彻底消融于水波之中、船上符灯挣扎着想要重燃的刹那,苏
夜白清晰地看到,船头那几名水鬼船夫的脸上,非但没有丝毫逃过一劫的庆幸,
反而流露出了一种近乎死寂的麻木。
他们默默地转过身,再次握住了那虚无的桨,准备推动这艘囚笼驶入无边的
夜河,重复那永无止境的劳役。
那无声的绝望,比任何凄厉的哭嚎都更令人心悸。
「尊神且慢!」一道清朗的声音划破了河面上的沉闷。
河神身形停顿了一下,他浑浊的目光略带诧异地投向这个突然开口的凡人。
苏夜白话一出口,自己也是一怔。
但事已至此,他迅速定下心神,对着河神虚影深深地作了一个揖,用恳切的
语气说道:「小生苏夜白,冒昧惊扰尊神,自知唐突,万望海涵。」
他直起身,目光迎向那神瞳,「并非是在下有意要僭越,只是在看见了这种
轮回无解的苦楚之后,我的心中实在是难以安宁。既然尊神说此局『根须已缠入
红尘』,敢问这红尘之中,可有能够斩断孽根的刀刃?可有能够涤荡污浊的方法?」
老河神凝视他片刻,目光中的诧异渐渐消散,缓缓道:「凡人之躯,竟然怀
有此等的慈悲心肠,也算是难得了。然而天地有序,神人各司其职。你难道没有
听过「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」这句话吗?」
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苏夜白,望向了霖安城深处,语气中带上了一丝讥诮:
「那位坐镇城中的『父母官』……呵,但愿他在享用人间香火的余暇,还能记得
睁开眼,管一管这发生在他城墙根下的腌臜事。」
河神顿了顿,最终好意地补充了一句:「少年人,心中有尺,量力而行。」
话音未落,河神身影已彻底化作涟漪,消散于河面之上。
那艘画舫的灯火重新亮起,缓缓驶向黑暗深处。
苏夜白立于河边,眉头紧锁。
背后的墨娘轻声叹道:「神意昭昭,其言也善。此事远非眼下能解,公子,
你已经问了该问的话,也尽了能尽的心力。」
苏夜白默然点头,只得将今日之事深深埋入心底。
此事过了数日,一位周身绫罗的富商满面愁容地登了门,请苏夜白为其画一
幅贺寿图。
才刚一落座,还未等墨研开,他便忍不住唉声叹气,大吐苦水。
他所抱怨的,正是前些夜里河上的那桩奇事。
「苏先生,您是不知道啊!我花了足足这个数——」
他伸出三根胖短的手指,激动地比划着,「——包下那『锦绣舫』,本来想
借着金道人的神通,给我家老泰山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寿宴,请的可都是霖安城里
有头有脸的人物!」
「谁知……谁知那船刚离岸,邪门的事就一桩接一桩!」富商的表情变得心
有余悸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夜晚。
「起初还好好的,可船一行到河心,就仿佛有什么东西……变了!」
「那请来的江南丝竹班子,手指头就跟被水鬼按住了一样,不受自己使唤!
那调子变得哟,凄惨得没法听!呜呜咽咽的,哪还是给人听的曲儿,根本就是河
底下那些淹死鬼在开丧堂会!听得我后脊梁骨一阵阵发麻,汗毛都竖起来了!」
「这还不算完!」
他拍着大腿,脸上血色尽褪,「窖藏三十年的女儿红,甭说酒香,连半点酒
气都无,反倒泛出一股子水草的腐烂味儿,一入口,哎呦喂,又咸又涩!」
他说到此处,竟下意识地干呕了一下,仿佛那滋味仍未散去。
「最骇人的是,」
富商压低了声音,「席间那点刚热络起来的劲儿『啪』一下就断了,紧接着
就像有无数双湿冷的手在抚摸所有人的后背,要把自个儿心里那点见不得光的苦
楚和委屈全都给掏了出来。不知是谁先起的头,竟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诉起人生艰
难……紧接着大家就跟中了邪一样,有一个算一个,都在那儿不是哀叹命如草芥
身不由己,就是在哭嚎永无出头之日!」
他摊开双手,一脸的匪夷所思:「您说说!好好的一场寿宴,硬生生变成了
一场百十来号人被附身般的哭丧!自打那日起,莫说是我,这满城谁还敢再上那
显了形露了馅的鬼画舫?金道人这棵摇钱树,算是彻底倒了!」
等到送走那兀自喋喋不休的富商,苏夜白独自坐案前,心中已是波澜万丈。
当天夜里,他鬼使神差般再次来到夜泊河畔。
只见河面之上,月华清冷如霜,映照着死一般的寂静。
昔日彻夜不息的喧嚣灯火早已湮灭,那数十艘曾极尽奢华的画舫,此刻皆如
被抽去了魂魄的巨兽骸骨,无声无息地蛰伏在浓稠的黑暗里,再无一丝生机。
然而,就在这片彻底的死寂之中,苏夜白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
痕迹。
在一艘最大画舫的船舷吃水线附近,月光照亮了一小片区域。
那里的木质并非腐朽,而是呈现出一种异常焦黑干燥的状态,仿佛被某种力
量精准地灼炼过,并未伤及周围分毫,只留下一道清晰无比的焦痕指印。
苏夜白凝视着那绝非自然形成的痕迹,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掠过脑海那金
道人的邪术绝非自行败露,而是被人以摧枯拉朽的手段猛然戳破,才泄露出这般
不堪的里子他背后的墨娘声音幽幽响起:「这霖安城,是来了一位『净街扫尘」
的厉害人物了。」
苏夜白默然不语。
他最后望了一眼那死寂的河面,转身融入夜色之中。
风,已起于青萍之末。
第十二章:兵
霖安城郊外有一座无名的小山丘,山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不晓年岁老柳树。
在城中樵夫与药农间流传着一桩奇谈。
都说月上中天时,若有胆大之人路过那山丘,便能瞧见一桩诡异又滑稽的景
象:数十只麻雀、蛤蟆、野兔、黄鼠狼,但凡是能喘气儿的活物,竟都在那老柳
树下,排成一列歪歪扭扭、不成体统的队列,仿佛在听一位看不见的「将军」训
话。
这个传闻勾起了苏夜白的兴趣。
在这一天的夜里,月光如同流水,他携带了那幅《素衣吟月图》,独自一人,
向着那座山丘行去。
临近山丘,他并不急于现身,而是先隐藏在了一块巨大的岩石之后,运起目
力望去。
月光清明,照见那队列前方正立着一位老者魂灵,他身上穿着残破的旧式军
服,面容早被风霜刻满沟壑。
他如钢钉般钉在原地,目光如同闪电一般射向那列乌合之众,口中发出低沉
而严厉的训斥。
只见队列最前头的一只肥兔子打了个盹,身子一歪。
那老兵魂灵顿时怒目圆睁,他虚虚一挥手,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拍在兔子身上,
惊得它慌忙挺直身子,就连耳朵都竖得笔直。
旁边一只蛤蟆刚要发出「呱」的叫声,立刻就被老兵严厉的目光瞪得把声音
憋了回去,只鼓了鼓腮帮子。
苏夜白看得分明,那老者的魂灵周身有清气环绕,并非恶类,只是那份执念
的深度已经化为了实质。
他的心中好奇更甚,于是便从岩后缓步走出,对着那老兵魂灵恭恭敬敬地行
了个长揖:「晚辈苏夜白,偶然经过此地,看见老先生治军严谨,心中实在是钦
佩,冒昧叨扰。」
那老兵魂灵见苏夜白不仅能看见自己,还毫不畏惧,眼中讶异之色一闪而过,
转而露出一种积年累月的疲沓。
他好像是终于逮着一个能搭话的活人,把满腹牢骚都倒了出来,沙哑嗓子裹
着粗豪气,劈头就说道:「你这后生,眼力倒是不差!」
老兵魂灵粗声喝道。
他虚指着那列歪七扭八的「队伍」,声音里满愤懑:「来得正好!快来替老
子评评理!」
「瞧瞧!瞧瞧老子手底下这群怂兵!」
他手指一划,扫过那群禽兽:「我叫它们站,却没有个站的样子;叫它们坐,
也没有个坐的样子!这军列歪斜,倒像是一条蛇在爬,一条蚯蚓在拱!」
指头又猛地戳向刚才打瞌睡的那只肥兔子:「还有那夯货!在值哨的时候,
竟然敢于瞌睡!如果是在当年,老子早就已经打了它二十军棍!」
接着扭头瞪向一旁鼓腮的蛤蟆:「还有那只癞蛤蟆!它的嘴一开口便是呱
呱的乱叫,这成何体统!此事乃是泄露军机,应当被判处重罪!」
他将手抱在胸前,胸膛起伏了一下。
最后像是把所有无奈都压进了一声闷哼里,摇头嗤笑道:「真是,一代不如
一代!」
他语气激愤,仿佛面对的真是千军万马。
但是在那愤怒的下面,却浸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。
苏夜白正不知道如何接话,却听得那老兵谈兴愈浓:「想当年,老子带着弟
兄们守这山头,三天三夜,打退了敌军一十八次冲锋,那箭矢插在身上就跟刺猬
似的……」
他的话音戛然而止。
方才还激愤的神情骤然之间便褪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一片枯槁。
那总是绷得板正的肩膀忽然就塌了几分,站在月光里晃了晃,就像是棵忽然
被风吹折了的老松。
最终所有未能说完的话语都混成一声粗重的叹息,散进夜风里,再听不见了。
恰好在这个时候,墨娘的声音轻轻落进苏夜白心神之中:「公子且慢……此
间的煞气是凝重的,然而忠烈之意却更为凛然,叫人不敢轻侮。」
她声气极轻,却字字清晰,宛若耳语:「方才这位军爷所说的话,倒让我想
起了往昔曾在书阁之中听闻的一件事——这个地方,在八十年之前,曾有过一支
杨姓的部队,为了保卫全城的生民,在此地结阵。兵尽矢穷,力战数日,最后全
师尽墨,无一人生还。」
在听闻了墨娘的这番话之后,苏夜白再去看那个老兵魂灵的时候,其目光已
全然不同。
眼前的景象,又如何能够用「练兵」之说来解释呢?
这分明是一场经历了八十载寒暑而不曾改变的驻守,是一位孤单的魂魄恪守
着他那早已不被任何人所记取的职责,等候着一封永不可能抵达的兵符。
苏夜白只觉得自己喉头一哽,鼻尖发酸,他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画卷。
他并未点破那悲壮的往事,只是再次深深一揖,神色愈发恭敬:「老前辈,
您在此地戍守,劳苦功高。如今天下承平,霖安繁华远胜往昔,百姓安居乐业。」
他目光清亮地看着老兵那空洞的双眼,提出了个古怪的请求:「晚辈想要用
这支笔,为您绘制一幅今日霖安城的「沙盘阵图」,邀您检阅一番。您看可好?」
「检阅?」
那老兵魂灵闻言,先是感到茫然,随即那双因执念而略显浑浊的眸子,如同
被投入火星的干柴,迸发出惊人的亮光!
「好!好!让老子看看!看看!」
苏夜白当即席地而坐,于老柳树下展卷研墨。
他笔走龙蛇,泼洒丹青。
然而他画的却非山川险隘,亦非兵戈铁马。
他所画的,是城中璀璨不夜的万家灯火,是熙攘喧闹的市井长街,是巷弄里
追逐纸鸢的垂髫小儿,是茶楼下悠然对弈的白头老翁。
他所画的,正是这个时代最平凡、却也最珍贵的太平景象。
当他为那画中千家万户的窗棂点上最后一笔昏黄时,奇异的景象便发生了!
整幅画卷蓦地漾开一片柔和而恢弘的光辉,如同将最温暖的夕阳余晖尽数熔
炼其中,瞬间驱散了山丘的夜寒与孤寂。
那老兵魂灵怔怔地望着画中景象。
在他那双浑浊的眼中,倒映着画中那从未见过的繁华。
便在这时,一阵苍凉而温柔的哼唱声,自画中一条深巷里悠悠传来——一位
白发老妪正轻拍着自己的孙儿,哼着一支古老的调子。
那歌声穿越八十载光阴,一字一句,清晰地叩击着他的心魄:「霖安城外哟,
三道梁,一道梁来一重伤。好男儿血沃青山下,不教胡马渡潇湘。哎嘿哟,青山
处处埋忠骨,魂灵悠悠护家乡……」
这歌声像一把锈蚀的钥匙,猛地捅开了记忆最深处的锁。
刹那间,烽火连天、弟兄们决绝的背影、城中父老含泪相送的目光……无数
画面奔涌而来。
他守护的、他失去的、他为之付出一切的,原来从未被遗忘,都已化作这街
头巷尾最寻常的安宁,融进了这血脉相传的歌谣里。
他那张浸满了风霜的面庞,在那古老的歌谣中一点一点地融化开来。
他挺直了身躯,整理了一下破旧的军服,庄重肃穆到了极点。
随后他转身面向那画中的太平盛世,用尽全身力气行了一个最标准的
军礼。
晨光熹微,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刺破云层,温柔地洒落在山丘之上。
那光芒与画上的辉光交融在一起。
在光影之中,那老兵魂灵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。
他的脸上带着满足而平和的笑容,如同是终于卸下了千斤的重担一般,安然
地随风消散。
苏夜白站在晨风之中,望着他消失的方向,久久无言。
手中的霖安城,在朝阳下显得愈发温暖而真实。
山风拂过,空余老柳寂寂。
他忽地挺直身躯,将手中画卷对着那空茫的山丘与万丈霞光,朗声喊道:
「霖安无恙——!」
声荡四野,群山回应。
「永世不忘。」
2025/09/03发表于:sis001
字数:7,283 字
第十一章:夜泊鬼舫
苏夜白自从得了墨娘为伴,画技与心境皆日渐精进。
只是墨娘终究是魂体,长久地寄身于画卷之内,仍然需要「人气」的滋养。
为此,苏夜白便时常将那幅《素衣吟月图》卷起,于夜间带在身边,一同游
览霖安城的城郭。
这一晚,他们二人来到了绕城而过的「夜泊河」畔。
这条河白日里是千帆竞渡、货运繁忙的交通要道;而一入夜,便摇身变成了
这富庶之地的销金之窟。
甫一靠近南岸码头,那喧嚣的人声与奢华的灯火便如同热浪扑面而来。
只见河面之上,有数十艘雕梁画栋的豪华画舫往来穿梭,明角灯将整片水域
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,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丝竹管弦之悠扬、行酒猜令之豪放、莺歌燕语之娇俏,种种声浪交织盘旋不绝于耳,竟然将夏夜的虫鸣与风声都给彻底地压了下去。
画中的墨娘沉默了半晌,河面上过于炽烈的光晕似乎让她有些不适。
过了很久,方才用带着几分疏离的声调轻声说道:「在百年之前,此地的水
汽是清冽的,澄净的江面如同白练。
夜间唯有渔火二三,与天上疏星相互映照,方有能照见「月照孤舟」的冷寂
之趣。」
她接着的话锋微微一转,语气中染上难以察觉的惋惜:「而今这般,竟是将
天地间的清辉与幽寂都驱赶殆尽了。
这般汲汲营营的声势,美则美矣,只是却失了真意,落了下乘。」
「当真是,换了人间。」
她慨叹的余音还未散去,便被岸边码头上一阵更鼎沸的声浪所淹没了。
只见那码头上人头攒动,全都是是些衣着华贵的富商巨贾、佩刀挂剑的江湖
豪客,他们正争先恐后地等候着登船。
人群中不时传来几句高谈阔论,声音一个比一个响亮,仿佛要将那画舫上的
丝竹声都给压下去:「王员外出手阔绰!我听闻方才在「锦绣舫」,那柄前朝的
玉如意竟被他以三百两拍了去!」
「那又算得了什么?李公子今夜与人在「天香舫」上对赌,一注便下了一百
两黄金!」
苏夜白听着这些动辄千金的豪赌,再摸了摸自己袖中那几两用来买茶点的碎
银,两相对比之下,不免哑然失笑。
画中的墨娘似被他的笑意感染,那清冷的声线里也透出一份人间烟火气的莞
尔:「如此繁华,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句旧诗,『瑶台璎琳,皆有其价;仙宫咫尺,
凡人无路』。公子,看来你我今夜便只能充当那隔岸观火之人了。」
苏夜白正想要回应,忽然看见一艘最为瑰丽的画舫,劈开倒映着灯火的金色
水波,如一座浮华不夜的水上仙阙般缓缓驶近。
船上觥筹交错,影摇歌扇,宾客尽欢,一切看起来,都完美地诠释了何为
「人间乐土」。
然而,就在那画舫离得足够近,近到能数清歌女云鬓上的珠钗步摇的时候,
苏夜白脸上闲适笑意却倏然冷却。
在他的眼中,那船竟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。
那悦耳的丝竹之声,变得如同鬼魅的呢喃,空洞而诡异;满船的珍馐佳酿,
竟嗅不出半分香气。
再看那些船夫歌女,方才还笑容可掬,此刻细看,却是个个面色青白。
他们脚步虚浮,周身缠绕着一股驱不散的湿冷阴气。
这种情绪上的骤然变化也清晰地透过画卷,传递给了其中的墨娘。
「公子?这船有什么不妥之处吗?」
苏夜白目光一凛,他一字一句地轻声说道:「船是好船,景也是好景……」
「只是这船上,有鬼。」
二人正交谈间,异变陡生!
河中央最大的一艘画舫,其上灯火在此刻骤然尽数熄灭!船身猛地一滞,如
同被无形巨手死死攥住,戛然钉死在原地!
这毫无征兆的剧烈顿挫,瞬间撕裂了所有虚妄的欢宴。
船楼内玉碎瓷迸,哗啦作响,酒浆果馔泼洒一地;方才的管弦之声被一片惊
声尖叫与惊怒交加的厉声呵问彻底取代。
「怎么回事!」
「稳住!船夫都死到哪里去了?!」
「哎呦!我的袍子!」
河水剧烈翻腾,推搡着失控的画舫使其左倾右斜,更引得船上哭爹喊娘,乱
作一团。
就在这片凡俗混乱的正中央。
一位身披苔衣、须发皆为水草的老河神从浊水中缓缓升腾而起。
那些惊慌失措的宾客对此毫无察觉,依旧对着空气与流水叫骂不休。
他无视了船上凡人的骚动,那宛若实质的目光死死盯住船头那掌舵的青面船
夫。
其声如闷雷炸响:「大胆孽障!你们竟敢驱使这种污秽的鬼力,来玷污我的
清流!」
那青面船夫的魂体被这蕴含神威的怒喝震得几欲溃散,扑倒在地,叩首不止:
「河神老爷息怒!非是小鬼自作主张,实在是……实在是身不由己啊!」
「还敢狡辩!」
河神怒喝打断,「往日里,你们虽然使用鬼力,却还知道收敛,不过就是让
船快一些、静一些!我念在你们也是可怜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也罢了!」
他巨大的手掌猛地指向那艘画舫,指尖水汽凝聚:「可今日你们竟敢在
此处布下邪阵来窃夺整条水脉的灵气,以此供养那迷惑人心神的邪法,好让凡人嬉戏!」
苏夜白闻言凝神望去,果然看见画舫吃水线之下,似乎有数道幽暗的符文随
着水波若隐若现。
「水脉枯竭一寸,我的身体便会损伤一分!」
河神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金石崩裂般的怒意与痛楚:「你们真当我是泥塑
的木偶,毫无知觉吗?!」
「河神老爷明鉴!我等皆是沉溺此河的孤魂野鬼,受那百年冰水蚀骨之刑乃
是天定的命数!可恨那『金道人』,他先是用重入轮回的虚假言语来诓骗我们,
引诱我等签下那逃不脱的卖身契;再施行那邪法将我等的残魂与这船炼在了一处,
永世不得超生!」
「他逼我等日夜驱动这『汲灵水阵』,偷来的灵气都输送到舫心那盏琉璃灯
里,去维持什么『幻梦术』,让那些客人醉生梦死,才好赚上他们的金银啊!」
「说起来真是可笑可悲。生前为人奔波劳碌,卖命换那几两糊口的银钱;死
后成了鬼,竟还是换了个地方当牛做马!永无出头之日!求河神老爷……垂怜啊!」
老河神听完这番血泪控诉,那由水流构成的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。
他环顾着这片被「买卖」二字熏得油腻污浊的水域,目光最终落回那些瑟瑟
发抖的可怜虫身上。
他周身水汽如沸,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。
然而那澎湃的力量却在触及某种无形界限的瞬间,硬生生倒卷回流,未能向
画舫倾泻分毫。
他滔天的怒火,在一声几乎要将整条河都压得下沉的漫长叹息中,被强行摁
熄。
「此间的孽债,根须已扎上岸,缠入了霖安城的滚滚红尘。」
老河神的声音低沉下去,「我只能管辖这水里的事情。至于水上的船,船上
的人,以及人所订立的契约,都并非是我所能够触及的。」
「你们……自求多福吧……」言罢,神躯便欲化水散去。
就在那神影即将彻底消融于水波之中、船上符灯挣扎着想要重燃的刹那,苏
夜白清晰地看到,船头那几名水鬼船夫的脸上,非但没有丝毫逃过一劫的庆幸,
反而流露出了一种近乎死寂的麻木。
他们默默地转过身,再次握住了那虚无的桨,准备推动这艘囚笼驶入无边的
夜河,重复那永无止境的劳役。
那无声的绝望,比任何凄厉的哭嚎都更令人心悸。
「尊神且慢!」一道清朗的声音划破了河面上的沉闷。
河神身形停顿了一下,他浑浊的目光略带诧异地投向这个突然开口的凡人。
苏夜白话一出口,自己也是一怔。
但事已至此,他迅速定下心神,对着河神虚影深深地作了一个揖,用恳切的
语气说道:「小生苏夜白,冒昧惊扰尊神,自知唐突,万望海涵。」
他直起身,目光迎向那神瞳,「并非是在下有意要僭越,只是在看见了这种
轮回无解的苦楚之后,我的心中实在是难以安宁。既然尊神说此局『根须已缠入
红尘』,敢问这红尘之中,可有能够斩断孽根的刀刃?可有能够涤荡污浊的方法?」
老河神凝视他片刻,目光中的诧异渐渐消散,缓缓道:「凡人之躯,竟然怀
有此等的慈悲心肠,也算是难得了。然而天地有序,神人各司其职。你难道没有
听过「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」这句话吗?」
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苏夜白,望向了霖安城深处,语气中带上了一丝讥诮:
「那位坐镇城中的『父母官』……呵,但愿他在享用人间香火的余暇,还能记得
睁开眼,管一管这发生在他城墙根下的腌臜事。」
河神顿了顿,最终好意地补充了一句:「少年人,心中有尺,量力而行。」
话音未落,河神身影已彻底化作涟漪,消散于河面之上。
那艘画舫的灯火重新亮起,缓缓驶向黑暗深处。
苏夜白立于河边,眉头紧锁。
背后的墨娘轻声叹道:「神意昭昭,其言也善。此事远非眼下能解,公子,
你已经问了该问的话,也尽了能尽的心力。」
苏夜白默然点头,只得将今日之事深深埋入心底。
此事过了数日,一位周身绫罗的富商满面愁容地登了门,请苏夜白为其画一
幅贺寿图。
才刚一落座,还未等墨研开,他便忍不住唉声叹气,大吐苦水。
他所抱怨的,正是前些夜里河上的那桩奇事。
「苏先生,您是不知道啊!我花了足足这个数——」
他伸出三根胖短的手指,激动地比划着,「——包下那『锦绣舫』,本来想
借着金道人的神通,给我家老泰山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寿宴,请的可都是霖安城里
有头有脸的人物!」
「谁知……谁知那船刚离岸,邪门的事就一桩接一桩!」富商的表情变得心
有余悸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夜晚。
「起初还好好的,可船一行到河心,就仿佛有什么东西……变了!」
「那请来的江南丝竹班子,手指头就跟被水鬼按住了一样,不受自己使唤!
那调子变得哟,凄惨得没法听!呜呜咽咽的,哪还是给人听的曲儿,根本就是河
底下那些淹死鬼在开丧堂会!听得我后脊梁骨一阵阵发麻,汗毛都竖起来了!」
「这还不算完!」
他拍着大腿,脸上血色尽褪,「窖藏三十年的女儿红,甭说酒香,连半点酒
气都无,反倒泛出一股子水草的腐烂味儿,一入口,哎呦喂,又咸又涩!」
他说到此处,竟下意识地干呕了一下,仿佛那滋味仍未散去。
「最骇人的是,」
富商压低了声音,「席间那点刚热络起来的劲儿『啪』一下就断了,紧接着
就像有无数双湿冷的手在抚摸所有人的后背,要把自个儿心里那点见不得光的苦
楚和委屈全都给掏了出来。不知是谁先起的头,竟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诉起人生艰
难……紧接着大家就跟中了邪一样,有一个算一个,都在那儿不是哀叹命如草芥
身不由己,就是在哭嚎永无出头之日!」
他摊开双手,一脸的匪夷所思:「您说说!好好的一场寿宴,硬生生变成了
一场百十来号人被附身般的哭丧!自打那日起,莫说是我,这满城谁还敢再上那
显了形露了馅的鬼画舫?金道人这棵摇钱树,算是彻底倒了!」
等到送走那兀自喋喋不休的富商,苏夜白独自坐案前,心中已是波澜万丈。
当天夜里,他鬼使神差般再次来到夜泊河畔。
只见河面之上,月华清冷如霜,映照着死一般的寂静。
昔日彻夜不息的喧嚣灯火早已湮灭,那数十艘曾极尽奢华的画舫,此刻皆如
被抽去了魂魄的巨兽骸骨,无声无息地蛰伏在浓稠的黑暗里,再无一丝生机。
然而,就在这片彻底的死寂之中,苏夜白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
痕迹。
在一艘最大画舫的船舷吃水线附近,月光照亮了一小片区域。
那里的木质并非腐朽,而是呈现出一种异常焦黑干燥的状态,仿佛被某种力
量精准地灼炼过,并未伤及周围分毫,只留下一道清晰无比的焦痕指印。
苏夜白凝视着那绝非自然形成的痕迹,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掠过脑海那金
道人的邪术绝非自行败露,而是被人以摧枯拉朽的手段猛然戳破,才泄露出这般
不堪的里子他背后的墨娘声音幽幽响起:「这霖安城,是来了一位『净街扫尘」
的厉害人物了。」
苏夜白默然不语。
他最后望了一眼那死寂的河面,转身融入夜色之中。
风,已起于青萍之末。
第十二章:兵
霖安城郊外有一座无名的小山丘,山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不晓年岁老柳树。
在城中樵夫与药农间流传着一桩奇谈。
都说月上中天时,若有胆大之人路过那山丘,便能瞧见一桩诡异又滑稽的景
象:数十只麻雀、蛤蟆、野兔、黄鼠狼,但凡是能喘气儿的活物,竟都在那老柳
树下,排成一列歪歪扭扭、不成体统的队列,仿佛在听一位看不见的「将军」训
话。
这个传闻勾起了苏夜白的兴趣。
在这一天的夜里,月光如同流水,他携带了那幅《素衣吟月图》,独自一人,
向着那座山丘行去。
临近山丘,他并不急于现身,而是先隐藏在了一块巨大的岩石之后,运起目
力望去。
月光清明,照见那队列前方正立着一位老者魂灵,他身上穿着残破的旧式军
服,面容早被风霜刻满沟壑。
他如钢钉般钉在原地,目光如同闪电一般射向那列乌合之众,口中发出低沉
而严厉的训斥。
只见队列最前头的一只肥兔子打了个盹,身子一歪。
那老兵魂灵顿时怒目圆睁,他虚虚一挥手,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拍在兔子身上,
惊得它慌忙挺直身子,就连耳朵都竖得笔直。
旁边一只蛤蟆刚要发出「呱」的叫声,立刻就被老兵严厉的目光瞪得把声音
憋了回去,只鼓了鼓腮帮子。
苏夜白看得分明,那老者的魂灵周身有清气环绕,并非恶类,只是那份执念
的深度已经化为了实质。
他的心中好奇更甚,于是便从岩后缓步走出,对着那老兵魂灵恭恭敬敬地行
了个长揖:「晚辈苏夜白,偶然经过此地,看见老先生治军严谨,心中实在是钦
佩,冒昧叨扰。」
那老兵魂灵见苏夜白不仅能看见自己,还毫不畏惧,眼中讶异之色一闪而过,
转而露出一种积年累月的疲沓。
他好像是终于逮着一个能搭话的活人,把满腹牢骚都倒了出来,沙哑嗓子裹
着粗豪气,劈头就说道:「你这后生,眼力倒是不差!」
老兵魂灵粗声喝道。
他虚指着那列歪七扭八的「队伍」,声音里满愤懑:「来得正好!快来替老
子评评理!」
「瞧瞧!瞧瞧老子手底下这群怂兵!」
他手指一划,扫过那群禽兽:「我叫它们站,却没有个站的样子;叫它们坐,
也没有个坐的样子!这军列歪斜,倒像是一条蛇在爬,一条蚯蚓在拱!」
指头又猛地戳向刚才打瞌睡的那只肥兔子:「还有那夯货!在值哨的时候,
竟然敢于瞌睡!如果是在当年,老子早就已经打了它二十军棍!」
接着扭头瞪向一旁鼓腮的蛤蟆:「还有那只癞蛤蟆!它的嘴一开口便是呱
呱的乱叫,这成何体统!此事乃是泄露军机,应当被判处重罪!」
他将手抱在胸前,胸膛起伏了一下。
最后像是把所有无奈都压进了一声闷哼里,摇头嗤笑道:「真是,一代不如
一代!」
他语气激愤,仿佛面对的真是千军万马。
但是在那愤怒的下面,却浸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。
苏夜白正不知道如何接话,却听得那老兵谈兴愈浓:「想当年,老子带着弟
兄们守这山头,三天三夜,打退了敌军一十八次冲锋,那箭矢插在身上就跟刺猬
似的……」
他的话音戛然而止。
方才还激愤的神情骤然之间便褪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一片枯槁。
那总是绷得板正的肩膀忽然就塌了几分,站在月光里晃了晃,就像是棵忽然
被风吹折了的老松。
最终所有未能说完的话语都混成一声粗重的叹息,散进夜风里,再听不见了。
恰好在这个时候,墨娘的声音轻轻落进苏夜白心神之中:「公子且慢……此
间的煞气是凝重的,然而忠烈之意却更为凛然,叫人不敢轻侮。」
她声气极轻,却字字清晰,宛若耳语:「方才这位军爷所说的话,倒让我想
起了往昔曾在书阁之中听闻的一件事——这个地方,在八十年之前,曾有过一支
杨姓的部队,为了保卫全城的生民,在此地结阵。兵尽矢穷,力战数日,最后全
师尽墨,无一人生还。」
在听闻了墨娘的这番话之后,苏夜白再去看那个老兵魂灵的时候,其目光已
全然不同。
眼前的景象,又如何能够用「练兵」之说来解释呢?
这分明是一场经历了八十载寒暑而不曾改变的驻守,是一位孤单的魂魄恪守
着他那早已不被任何人所记取的职责,等候着一封永不可能抵达的兵符。
苏夜白只觉得自己喉头一哽,鼻尖发酸,他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画卷。
他并未点破那悲壮的往事,只是再次深深一揖,神色愈发恭敬:「老前辈,
您在此地戍守,劳苦功高。如今天下承平,霖安繁华远胜往昔,百姓安居乐业。」
他目光清亮地看着老兵那空洞的双眼,提出了个古怪的请求:「晚辈想要用
这支笔,为您绘制一幅今日霖安城的「沙盘阵图」,邀您检阅一番。您看可好?」
「检阅?」
那老兵魂灵闻言,先是感到茫然,随即那双因执念而略显浑浊的眸子,如同
被投入火星的干柴,迸发出惊人的亮光!
「好!好!让老子看看!看看!」
苏夜白当即席地而坐,于老柳树下展卷研墨。
他笔走龙蛇,泼洒丹青。
然而他画的却非山川险隘,亦非兵戈铁马。
他所画的,是城中璀璨不夜的万家灯火,是熙攘喧闹的市井长街,是巷弄里
追逐纸鸢的垂髫小儿,是茶楼下悠然对弈的白头老翁。
他所画的,正是这个时代最平凡、却也最珍贵的太平景象。
当他为那画中千家万户的窗棂点上最后一笔昏黄时,奇异的景象便发生了!
整幅画卷蓦地漾开一片柔和而恢弘的光辉,如同将最温暖的夕阳余晖尽数熔
炼其中,瞬间驱散了山丘的夜寒与孤寂。
那老兵魂灵怔怔地望着画中景象。
在他那双浑浊的眼中,倒映着画中那从未见过的繁华。
便在这时,一阵苍凉而温柔的哼唱声,自画中一条深巷里悠悠传来——一位
白发老妪正轻拍着自己的孙儿,哼着一支古老的调子。
那歌声穿越八十载光阴,一字一句,清晰地叩击着他的心魄:「霖安城外哟,
三道梁,一道梁来一重伤。好男儿血沃青山下,不教胡马渡潇湘。哎嘿哟,青山
处处埋忠骨,魂灵悠悠护家乡……」
这歌声像一把锈蚀的钥匙,猛地捅开了记忆最深处的锁。
刹那间,烽火连天、弟兄们决绝的背影、城中父老含泪相送的目光……无数
画面奔涌而来。
他守护的、他失去的、他为之付出一切的,原来从未被遗忘,都已化作这街
头巷尾最寻常的安宁,融进了这血脉相传的歌谣里。
他那张浸满了风霜的面庞,在那古老的歌谣中一点一点地融化开来。
他挺直了身躯,整理了一下破旧的军服,庄重肃穆到了极点。
随后他转身面向那画中的太平盛世,用尽全身力气行了一个最标准的
军礼。
晨光熹微,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刺破云层,温柔地洒落在山丘之上。
那光芒与画上的辉光交融在一起。
在光影之中,那老兵魂灵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。
他的脸上带着满足而平和的笑容,如同是终于卸下了千斤的重担一般,安然
地随风消散。
苏夜白站在晨风之中,望着他消失的方向,久久无言。
手中的霖安城,在朝阳下显得愈发温暖而真实。
山风拂过,空余老柳寂寂。
他忽地挺直身躯,将手中画卷对着那空茫的山丘与万丈霞光,朗声喊道:
「霖安无恙——!」
声荡四野,群山回应。
「永世不忘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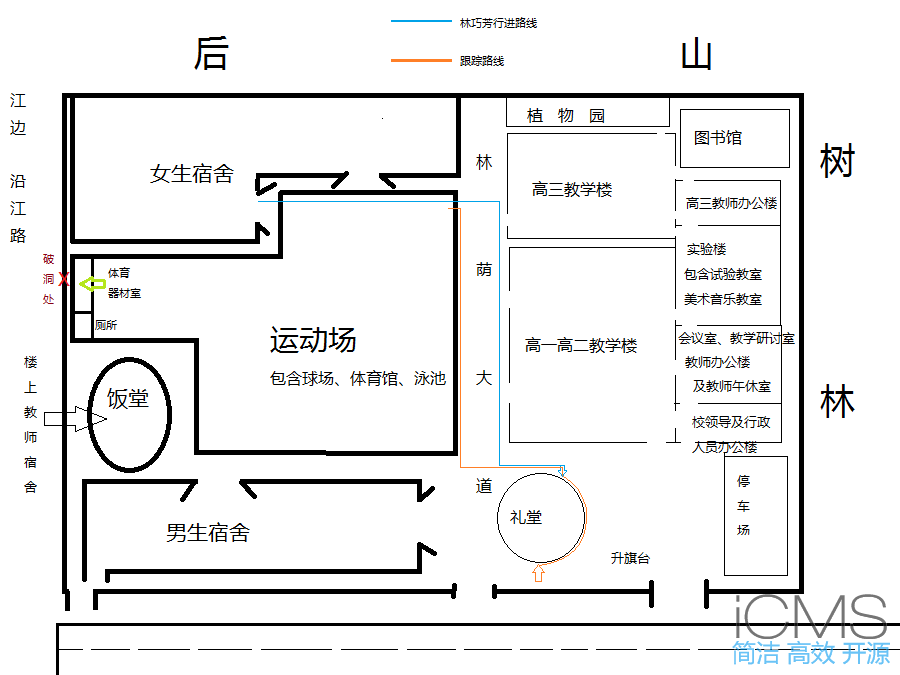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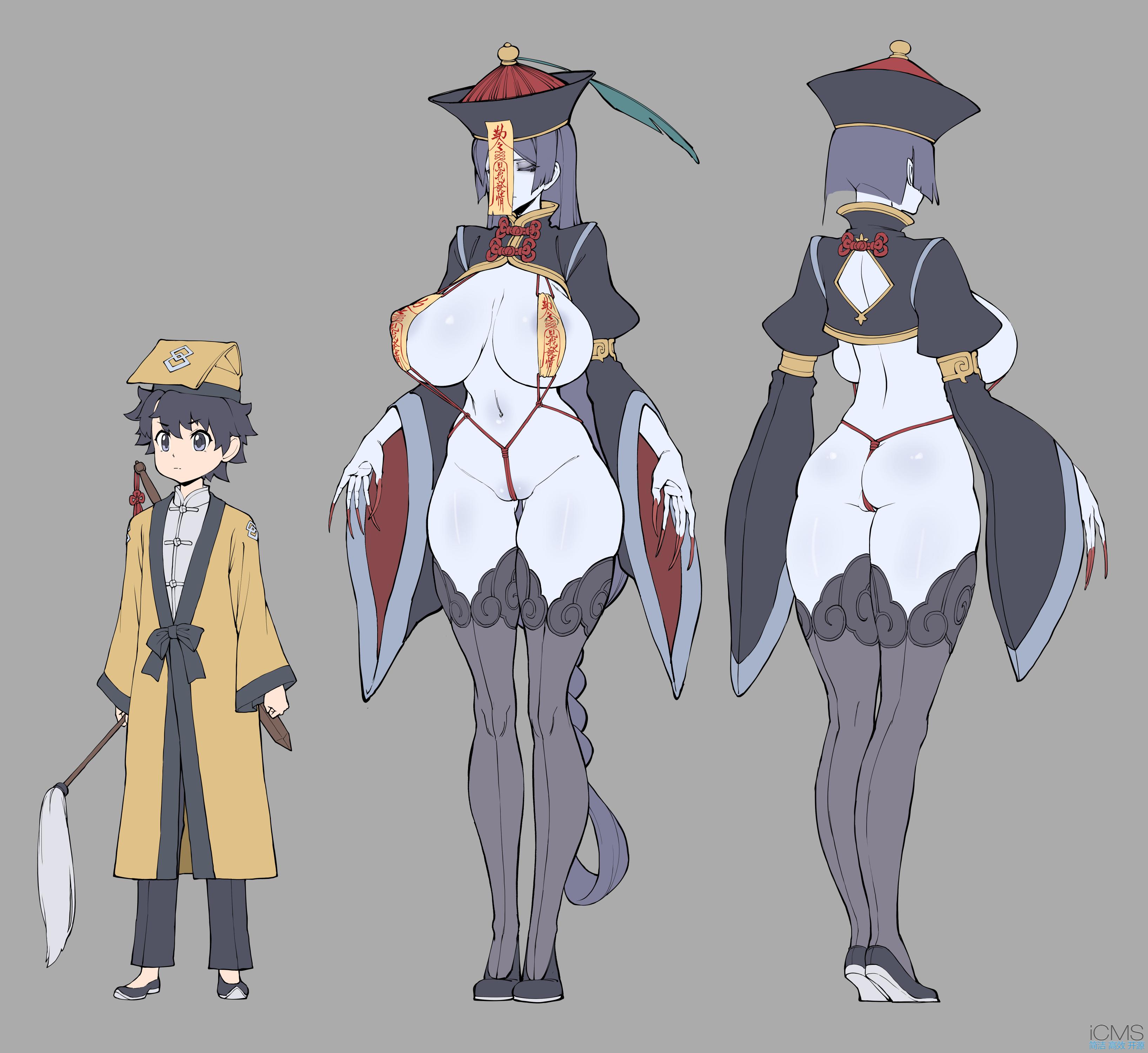

 加载中,请稍侯......
加载中,请稍侯......
精彩评论